跨性别污名化的呈现与转变:基于传播学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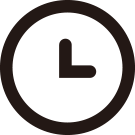 2021-12-18
2021-12-18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问题、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一书中认为,如今的二元性别观念是被建构的。
跨性别者的存在,无疑就是在打破这样的框架。
区别于生物意义上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塑造来源于社会建构(社会性别理论),而这种社会化的塑造离不开媒介传播。
作为社会化中介,媒介无时无刻不参与着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从报道要素来看,媒介对性别议题的报道主题、报道倾向以及话语呈现,都在向受众传递信息及态度,从而无形地反映、影响并建构着社会观念与行为。
在大众媒体方面,跨性别群体在其早期的议程设置中常处于边缘地位,新闻报道的可见度低,跨性别群体的话语权长期受到忽视。
学者陈建生认为:「弱势群体由于普遍缺乏能为他们代言、发声的渠道,不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从而影响了其利益的表达。」[1]
随着社会观念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跨性别群体从失语的状态逐渐觉醒为自主发声的群体,跨性别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受各种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关注。
媒体作为现实的渐近线,将跨性别议题选择性地呈现给受众。媒体对跨性别者的建构这一意义生产过程,也体现了当代社会性别意识。
本文关注跨性别群体的媒介生存境遇,并探讨媒介议题与性别身份的博弈。

性别二元框架下
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化呈现
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媒体的观念建构受限于社会观念。在传统的性别二元框架下,社会各界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化呈现明显。
「污名」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学术名词。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他人赋予的“丢脸特征”,而这种特征会使个体的身份“受损”。
在性别发展史中,跨性别者曾被冠以“病态”的污名化身份。医学界认为跨性别者有“性别认知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需要进行医疗干预令其“痊愈”。
在其它方面,跨性别者遭受的污名化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从“变性人”“人妖”和“伪娘”等病理性话语中可见一斑。
而媒体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化体现在早期的猎奇式报道中。
究其原因,在媒介市场化运作的背景下,媒体追求流量,进而迎合受众猎奇心理。
在跨性别群体的形象建构方面,媒体并不深挖跨性别群体的社会处境和精神世界,而是着重描绘这一不符合传统性别秩序的“奇观景象”。
2010年的快乐男声选手刘著因穿女装参赛而备受争议,并被冠以“伪娘”的名号。不少杂志媒体对刘著的烟熏妆和高跟鞋建构出猎奇色彩,并在采访中询问其是否要做“变性手术”。
针对外界的报道和舆论,刘著给出了回应:「头发是真的,声音是天生的。请允许这个世界有差异,可以不理解,但请别伤害。」
这种猎奇式报道的商业内核是身体消费,跨性别者的身体作为符号被消费。在消费社会(消费经济时代)背景下,消费的概念被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身体被资本力量高度商品化。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身体」的商品属性:「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2]
在消费社会,身体一词不仅意味着商业现象的掘金,更折射出独特的身体文化现象——人们的身体沦为娱乐的附庸。
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
一方面,污名化报道会导致受众对跨性别的误读。学者李文芬强调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要让公众了解跨性别知识,打破「无知」。[3]
另一方面,这种污名化会对跨性别者造成心理伤害。学者夏楠和刘爱忠将污名、歧视及其他偏见事件视为跨性别者心理健康的威胁压力源,并认为这容易导致抑郁、焦虑、自杀、药物滥用等心理卫生问题。[4]
污名化呈现的传播学解读
媒介现实与受众现实
这种猎奇式报道向大众展示了媒体重构的拟态环境,这种媒介现实区别于现实中的跨性别文化。
何为拟态环境呢?该学术名词由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
「大众传媒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以客观世界为蓝本塑造的、与客观世界有一定偏差的环境;拟态环境会制约人的认知与行为,并通过制约人的认知与行为而间接地对客观的现实世界产生影响。」[5]
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地球村愈加成为可能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更远、更久的信息。
但是,这种信息大多数不是通过我们自己亲身实践拿到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通过大众媒体,如报社、电视台和政府机构等众多的社会媒体组织对发生在世界上各个地点的事件进行一定的挑选,进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这其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播者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等的影响,也会受到组织机构的政治倾向、经济利益等的影响,所以它是一种有偏差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介现实去了解世界,那么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的回应,而是对「拟态环境」的解码。
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常常被受众投射到现实中,这就是「受众现实」,受众进而凭借媒介经验来审视现实生活中的跨性别者。
那么媒体对跨性别者的误读,会加剧公众的偏见与歧视。
媒介呈现中的身体规训
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媒体对跨性别群体的消费体现了身体的性别规训。
媒体所传递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并将其内化(社会强化),这种传媒和男权文化合谋的话语规训力量,使得跨性别群体在这个强大的话语权力场中遭受伤害。
美国学者Meyer提出的少数群体应激模型[6] 将内化污名作为跨性别者所遭受到的主要压力源之一,认为跨性别者会将受到的污名内化。
「规训」一词由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该观点从权力视角出发,探讨权力是如何内化并作用于人的意识,并最终实现对身体规训的。
规训发挥作用离不开媒介,也就是话语。通过话语对身体进行规训,其作用的结果则是把人向社会规范靠拢。该观点重点强调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
总而言之,在消费语境和文化工业背景下,权力机构利用规训权力对身体施加控制,其目的是得到一具听话的身体,以维护父权制。
因此,早期媒体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报道也是一种规训——通过病理性话语和情感叙事,跨性别者将性别二元的传播倾向内化,最终实现对身体规训的适应。

跨性别议题的转向
——性别二元对立的逐渐消解
媒体话语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互相推动。
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将“性别认同障碍/性别焦虑”更名为“性别不符”(注:ICD-11于2019年5月底正式获表决通过)。
同年1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
去病化和非罪化的社会制度进步推动了媒体的多元建构,媒体对于跨性别群体的关注也走向新的阶段。
近年来的媒介话语体现了性别二元对立框架的消解倾向,主流媒体的官方话语也逐渐转变。
2005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从性别观说开去》。评论员尊重性别的自由选择:「性别选择标志着人的选择权在扩大,标志着我们医药科学的发达,同时也标志着人在性别上开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胜利。」[7] 文章初步提出了跨性别平等理念。
2017年8月,人民网转载《中国妇女报》的报道《跨性别应是平等存在的正常性别:我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评析》,关注跨性别者的权益维护。
2020年2月,《法制日报》发表深度调查报道《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多数人有遭受校园暴力经历》,为跨性别群体发声,立志为其争取话语权、保障合法权益,认为性别认同是人的主体权利,「应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8]
2021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从社会性别规范看健康的性别差异》,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两个角度探讨健康状况,指出跨性别人群在卫生保健服务中遭受的污名和歧视,以及医疗资源的不足。
上述种种行为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对部分不了解跨性别议题的受众进行引导,使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跨性别群体的社会处境。
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9] 媒介话语就起到了一种召唤作用,大众媒体对跨性别议题的呼吁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会召唤受众进行学习。
当意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时,公众对跨性别群体便有了较高的包容度,这就是身份对行为的自我召唤;当文本内容在传播中引起更多的转发、评论和点赞时,社会召唤的影响应势而起。
结语: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认为,疯癫可能是一个时代同一个代际的集体意识中的恐惧,是社会大环境对于人们的影响。
学着从现象看到本质。媒体建构的跨性别议题对我们的启示在于,要清楚地认识到「是谁在阻止我认识外部世界」。在通往(认识)外部世界的路上,限制或影响我们的因素有很多,而刻板印象可能是其中主要的阻碍因素。
对性别的简单二元对立的心理根源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进入到传播学领域,始于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固定的成见』就像浇铸的铅版一样牢固,并且难以改变。」
一如李普曼所说,「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10]
我们可以把刻板印象看成是一个堡垒,在刻板印象的庇护下,我们可以在自我构建的舒适圈内随意批判他人;但是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偏见与歧视,会使我们丧失了对跨性别议题的理性认知。
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后,跨性别者不再过度失语,有了一定的话语机会和维权的媒介空间。
近年来的新闻报道也体现了对跨性别议题的逐步开放和当代社会对群体的人文关怀,但跨性别群体的媒介生存环境仍存在许多困境,在形式和结构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偏见与歧视等社会现象仍值得深思,平权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在多元性别视野下观察跨性别群体的生存,尊重跨性别者的性别多元化,这将促使社会性别文化多元化、健康化发展。
本文内容转载自网络 !原文作者:船思 侵权即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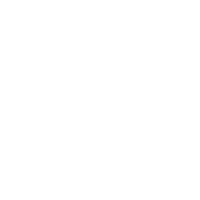


 180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