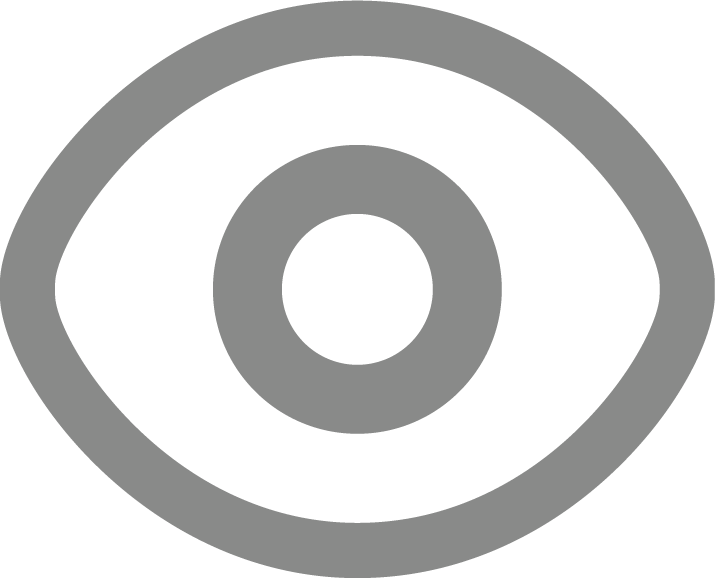在圈子中,是主导者更快乐,还是顺从者更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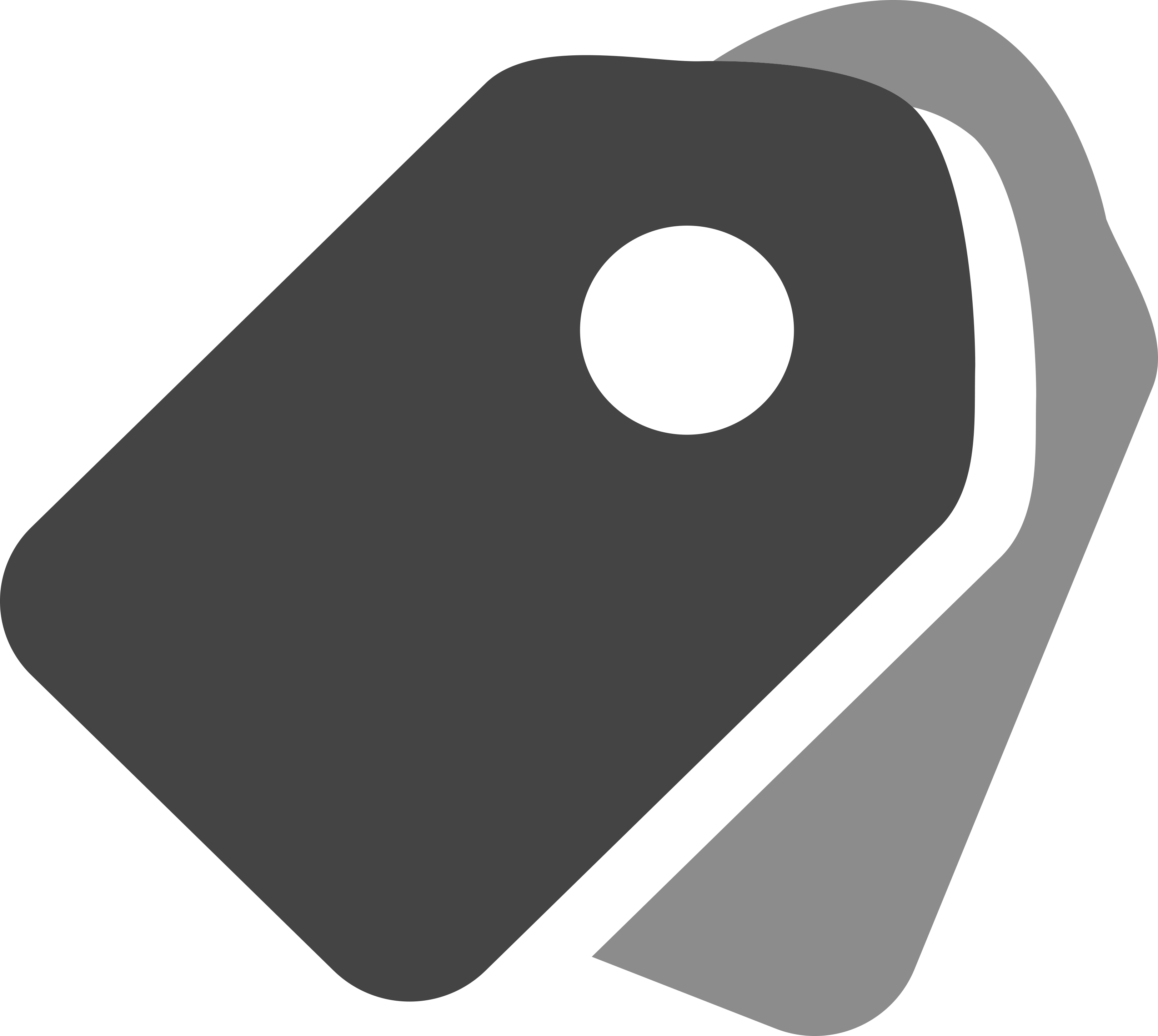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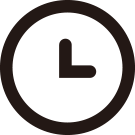 2025-09-16
2025-09-16在圈子中,是主导者更快乐,还是顺从者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圈子的快乐究竟源于哪里?到底哪个角色更容易获得快乐?
表面上看,似乎顺从者(或称“受虐者”)获得的满足感更多——至少从角色分布的比例来看是如此。在任何关系中,都存在主导与从属两种位置,而圈子中的主导者似乎相对稀缺。2008年加州某研究生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处于从属位置,占比约61%。另一方面,大约69%的男性完全或主要处于主导地位。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即那些角色可流动、既可主导也可顺从的人群,其具体比例尚不明确。但从社会观察来看,似乎偏好顺从角色的人更多。
男性主导者比例较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更符合传统的社会期待。因此,一部分男性可能被迫扮演“阿尔法”角色,成为表面上的主导者。处于从属位置可能让他们感到有失面子或不被允许。事实上,真正喜欢完全主导的男性比例并没有那么高。据国外某专业社群“FatLife”的统计,绝对掌控型的男性仅占24.76%,其他各类主导角色加起来总计约35.65%。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男性真正享受完全作为主导者——大约六成的人仍带有一定顺从特质,这也反映了人性中本来的复杂性。
人类天性中存在着一种向往“主体”的动力。主体对客体往往具有神秘的吸引力,甚至带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会让客体感到主体所给予的一切都是美好且充满魅力的。这种魅力往往源于客体内心深处的“不配得感”——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主体的一切付出都被视为莫大的恩赐和奖赏,哪怕只是一根头发、一片指甲,也可能被赋予神奇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甚至能看到某些精神领袖拍卖自己的头发,并且价格不菲。
基于这种心理机制,似乎可以推测,在施受虐关系中,顺从者可能获得更多快乐。基本前提在于,他们往往有更强烈的付出欲望,更愿意为对方奉献——而这正是亲密关系中最基本的快乐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一个普遍共识是:主导者(S)本质上是一位服务者,一个运用权力却居于高位的照顾者。在这种关系中,主导者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愿、照顾对方的感受,最大限度让另一方感到舒适——因为对方的舒适,恰是自己满足感的基础。这种关系最忌讳单方面的自我享乐。据说,S往往更为深情(具体是否如此尚不明确),但他们确实擅长倾听对方需求,揣摩对方的喜好,试探能最大化激发对方快乐的方式。这也成为主导者快乐的来源之一:一方面,他们享受支配行为本身,享受权力、命令和惩罚带来的掌控与力量感;另一方面,他们也依赖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即时反馈。
就像捏一个“惨叫鸡”——它之所以被捏,正是因为它会叫。如果得不到回应,这个动作就失去了意义。这类即时反馈是激活多巴胺的有效途径:我的动作立刻能换来你的反应。客体的回应越积极,就越说明“我做得成功”,这是一种被认可的快感,也能强化身份认同。就像别人大口吃你做的菜并且一脸享受,会加深你对自己厨艺的肯定。
而从属者(M)的快乐路径则完全不同。作为一个低位者,他们实际上是隐形的控制者和显性的享受者。其很多快乐正来自于前面提到的“不配得感”。大多数从属者无法直接控制主体,因为客体位置本就缺乏话语权。因此,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从属者会通过顺从、乖巧和讨好的方式争取主体的欢心——这很像一个孩子取悦父母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曾在某个阶段停滞,日后他就可能不断重复这个模式,尤其在亲密关系中不断重现原生家庭里的权力结构。通常来说,你在婚姻中的位置,就是你在原生家庭中的位置。
如果一个人在原生家庭中被过度剥夺了“主体感”,那么他在亲密关系中就可能特别渴望一个主体感强的对象,以此体验生命的完整。而施受虐关系,正是权力结构最为外显的一种形式。“主人”作为“奴隶”欲望的化身,能让奴隶体验到完整的主体感,以及残缺所带来的独特美感。
从属者的隐性控制体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主导者其实会完全遵从从属者的意见,不强迫其做不喜欢或做不到的事——这种尊重,可能在从属者的原生家庭中是从未获得过的。甚至,从属者仍可以要求主导者做某些事,哪怕是以恳求的方式表达,这种要求仍然有效,仍能获得回应。
当然,控制并不是从属者真正的享乐核心。他们更享受的是那种“你强大,我弱小;你高贵,我卑微;你拥有一切,我一无所有”的对立统一。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色,彼此依存才构成完整的图像。我用我的残缺衬托你的完美,你用你的完满凸显我的渺小。我们在一起,就象征着某种秩序与完整。这是一个近乎与“神”融合的过程——融合之后,我便有了归属,不再觉得自己残缺。
在这种深度的关系中,从属者会体验到一种“无我”的快乐,这也是他们主要的愉悦来源之一。从属者将自我完全交付出去,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从而卸下所有责任,完全依附对方,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做一个无需思考、没有负担的“婴儿”,甚至成为主人身体的一部分——一切决定和后果都由主人承担,自我彻底消解。
艾里希·弗洛姆将这种倾向称为“逃避自由”。人类喜欢逃避自由,是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越是追求自由,需要承受的代价就越多,责任带来压力,而人类天生不喜欢压力。作为一个婴儿,则是完全没有主体责任的,只需充当一个被支配的存在,其余一切都由对方承担。因此,人天生渴望融合与共生,因为与他者共生会带来安全感与轻松感,宛如找到一个可遮风挡雨的“神”。
《乌合之众》的底层逻辑也与此类似:个体融入一个庞大的有机体,成为其中一部分,从而逃避责任、享受共生带来的安心,仿佛回到母亲的子宫。因此这类群体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集体式的受虐心理——我们找到一个看似强大正确的理念或主义,依附进去,甚至借其之名肆意妄为。即使犯错,也能藏身群体之中,毕竟“法不责众”。
人类之所以渴望共生,部分是因为自感弱小,而与强大存在融合之后,他们就获得一种“虚假的强大感”,仿佛“我与某某一体”。信徒投入神的怀抱,从属者匍�于主人的脚下——这些都是融合的表现。与“他者”融合,意在补全自己的缺失。而在这个补全的过程中,当事人会体验到许多“临在”的快乐。
何为“临在”?它可以被理解为“如来”“要在未至”“将来未来”的状态——一种不确定的、充满张力的等待,能强烈激活多巴胺的分泌。实验表明,无论是狗还是猴子,它们在即将得到食物之前,多巴胺分泌水平最高。也就是说,生命体在未得到确定性之前,会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
那么在圈子中,什么时候是从属者最快乐的?就是这种“临在”状态:命令将至未至、惩罚将落未落之时。在惩罚的工具尚未真正落下之前,被惩罚者会进入一种既紧张又兴奋、既害怕又渴望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极为强烈的生命体验。
此外,渴望被满足之后也会带来快乐,且渴望越强烈,满足后的快感就越大。就像在干燥的沙漠中饥渴难耐时,一瓶清凉的水带来的爽快,远非平常喝水可比。人似乎有一种“享受匮乏”的倾向:匮乏越大,满足时带来的快乐就越多。
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痛苦具有肯定性,因为它是快乐的原点。痛苦提供足够的动力去消灭痛苦、获得快乐——但消灭之后,痛苦仍会再次出现。叔本华认为,苦是生命的根本常态,快乐只是短暂的间歇。这个观点或许也适用于圈子语境:一个人内心的创伤越大,他在圈子中可能获得的快乐就越多——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却深刻的现象。
也许,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爱的感受,圈子活动反而难以带给他太多快乐。一个内在饱满、没有匮乏与创伤的人格,可能不再需要借助施受虐关系去回溯或修复什么。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理论上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结、有缺失。去爱,就会让人想方设法补全缺损。而缺损过大的人,则可能在无意识中渴望通过施受虐关系,用疼痛与卑微去触摸关系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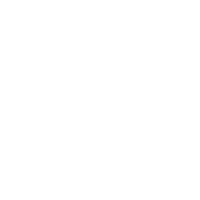

 180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