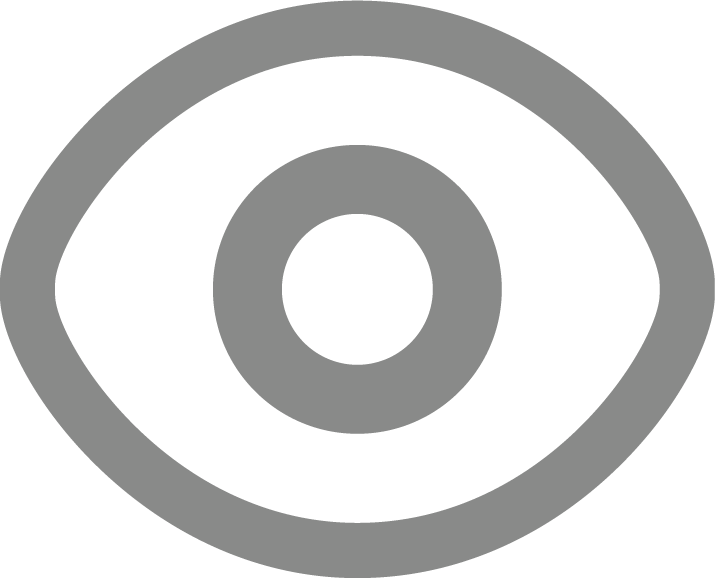从《捞女游戏》爆火,“捞女” 到底是操控欲望的 S还是臣服于结构的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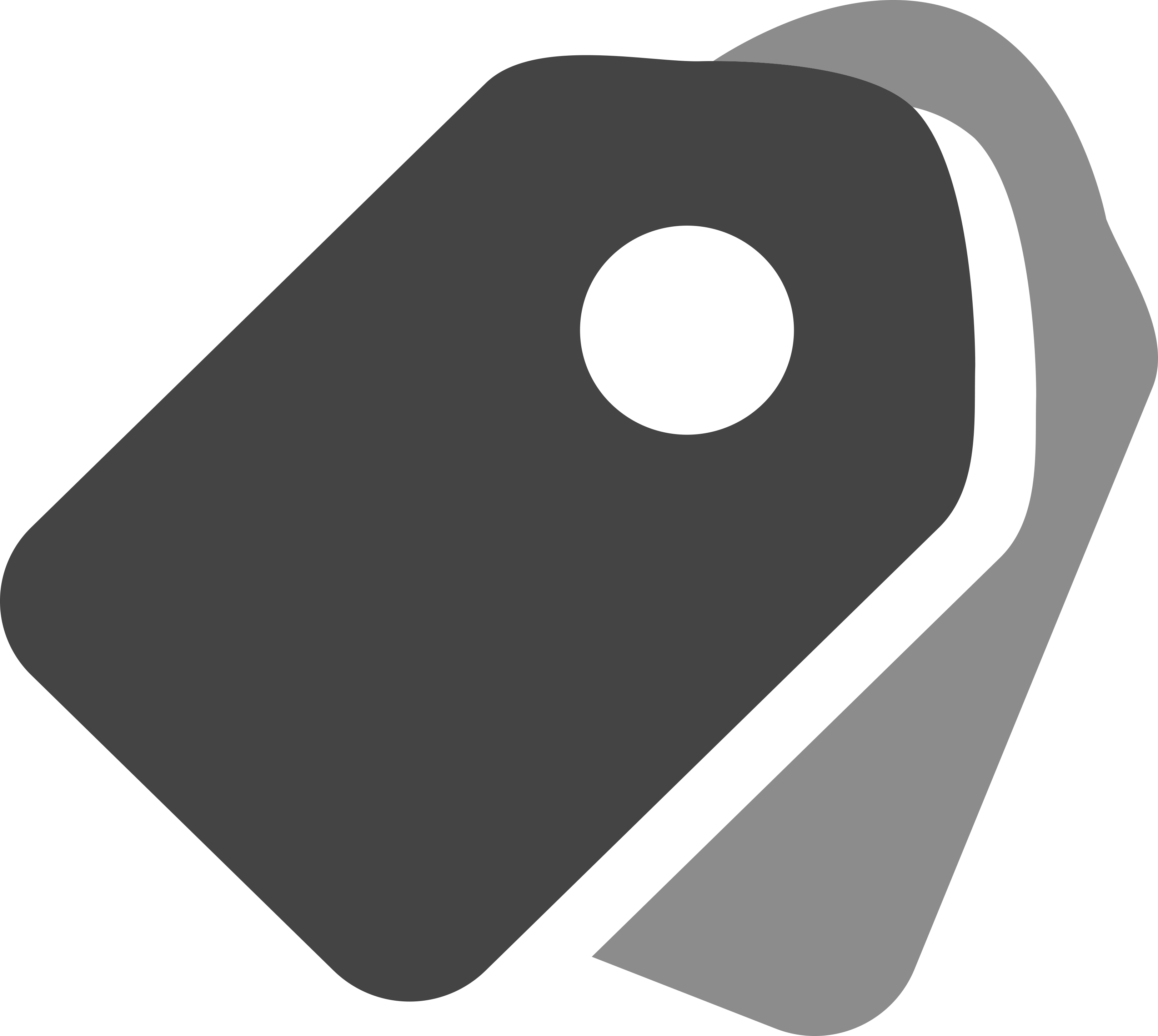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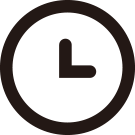 2025-07-31
2025-07-31从《捞女游戏》爆火,看背后复杂的情感与社会议题
2025 年 6 月,一款真人互动影像游戏在 Steam 上线后迅速蹿红,短短几天便冲上热搜榜首。它最初被叫做《捞女游戏》,后改名为《情感反诈模拟器》 ,其内容设定直给,玩家扮演曾被情感与金钱双重背叛的舔狗男,要在各类被设定为 “捞女” 的角色间周旋,练出火眼金睛,实现反杀,一雪前耻。
游戏爆火的同时,也掀起了激烈的争议浪潮。支持者觉得它撕开了现代情感骗局的伪装,给众多在情感中懵懂或受伤的男性提供了警示与宣泄口,不少男性玩家一边自嘲,一边沉浸在反杀的快感中,可见类似情感经历在现实里并非个例。反对者则痛批它是披着反诈外皮的性别歧视,将情感欺诈片面地归责于女性群体,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粗暴地简化成性别战争,加剧了两性对立。
撇去争议不谈,从精神分析视角深入剖析,“捞女” 这一现象远非一个简单的贬义标签,而是当下资本与权力欲望结构运作下的一种复杂症状。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里,理性过度扩张,情感被挤压出大片缺口,“捞女” 看似填补了这一空缺。她们投入的情感真真假假,即便有真情实意,也始终牢记 “捞” 的目标,客观上成了资本系统运转的特殊 “润滑剂”。
从宏观层面看,“捞女” 处于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她们试图操控情感关系来获取利益,看似在剥削男性,但实则自身也是这个结构中最先且最彻底被 “阉割” 的客体。她们的存在,是资本欲望结构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细究她们的成长背景,有的自幼在家庭中领悟到爱是需要交换的 “规则”;有的因贫困早早认定金钱等同于安全感;有的成长于情感淡漠、父爱缺席的家庭,试图通过讨好异性来确认自身价值;还有的在现实与网络中察觉到女性掌控关系就能掌控资源的 “逻辑”,进而主动训练自己成为猎手型人格。无论哪种成长路径,她们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往往不是爱,而是对曾经缺失之物的弥补。
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捞女” 到底是操控欲望的 S(施虐者,代表掌控),还是臣服于结构的 M(受虐者,代表臣服)呢?在大他者结构(象征着社会规范、语言、权力等构成的符号秩序)内来看,无人能真正自主决定自己的欲望,都只是在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捞女” 精准洞察父权体系下男性的欲望模式:男性被塑造为强者、控制者,背负着救世主幻想,其自我价值长期与这种形象绑定,现代性更是将男性欲望与资本深度捆绑。“捞女” 深谙这套认同逻辑,精准回应大他赋予女性的角色模板,将商品化、美貌货币化、情感权力化,把自身行为调节到最大限度满足资本与权力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她们是资本权力大他之下绝对的 M 人格,看似掌控,实则是对结构的深度臣服。
然而,若假设她们能从大他者结构中抽身而出,拥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进行主动操控,行为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此时,她们不再依赖男性给予的情感满足,而是通过理解与操控男性欲望本身获得快感与权力满足,精准调度男性的情绪、金钱和欲望投射。她们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与爱,只信奉利益机制与资源获取。表面的被动只是假象,其本质在于操控男性,让男性相信自己处于掌控地位。她们在关系中表演 M 的顺从,实则暗中试探男性情绪极限,验证自己的掌控力,是借助结构赋予的弱势身份,反向打破秩序,实现以弱胜强的权力反转,是隐藏在假 M 表象下的真正操控者。
在现实中,多数 “捞女” 并非固定处于 S 或 M 的某一极端,而是在两者之间游移切换。这种复杂的身份流动与矛盾性,构成了 “捞女” 现象独特又复杂的魅力。她们既是现代性伤痕的延伸,也是结构漏洞的穿透者;既是被凝视的符号,也是改写符号的 “黑客”。只要当下的资本与权力结构存在,“捞女” 这一现象必然会反复出现,这是结构的唯物必然性。但无论处于哪种状态,“捞女” 始终不是真正自由的主体,她们的行为始终在回应他人的目光,是大他者结构下训练出的特殊 “商品”,也是偶尔冲击现有结构的潜在 “骇客”。
《捞女游戏》的爆火,反映出当下社会情感信任的缺失与两性关系的紧张。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情感、性别、权力与资本复杂关系的窗口,也提醒着我们,要真正理解和解决这些社会议题,需要突破简单的性别对立思维,深入到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的深层去探寻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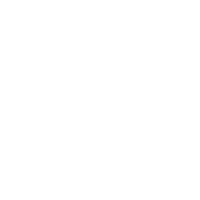

 180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