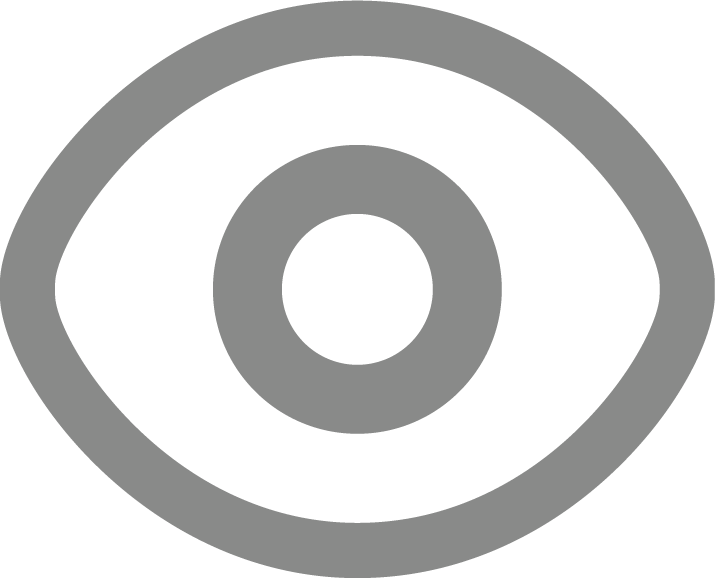深度解析:亲密关系中 “妈妈” 称谓背后的权力博弈与心理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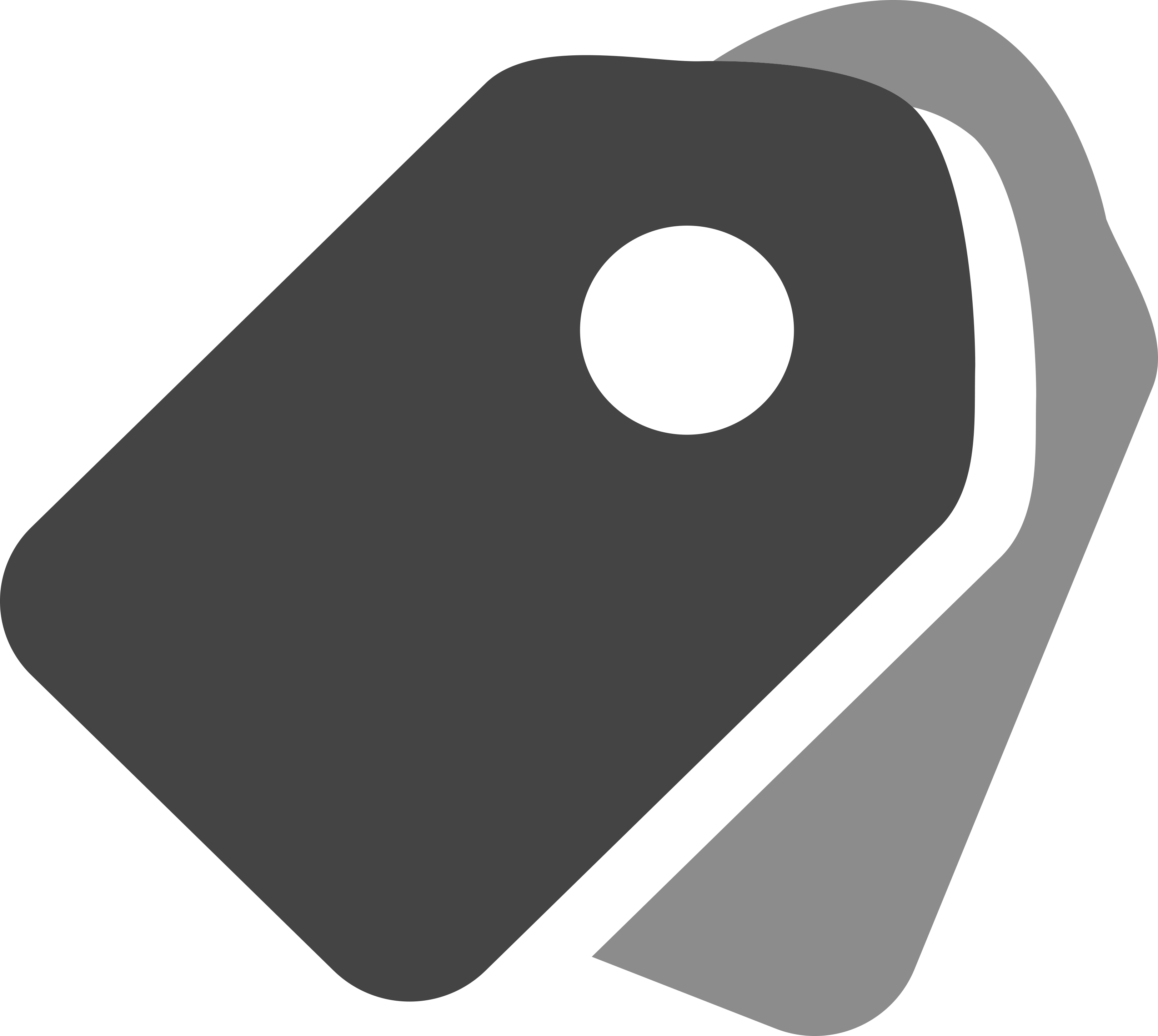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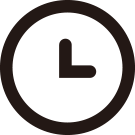 2025-07-06
2025-07-06深度解析:亲密关系中 “妈妈” 称谓背后的权力博弈与心理机制
一、从称谓到权力:一场被重构的性别游戏
当 “妈妈” 成为亲密关系中的情欲符号,它早已超越了血缘伦理的范畴。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年轻一代在传统性别秩序中寻求突围的心理投射 —— 通过羞耻感的解构,完成对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义。
- 支配欲的觉醒:从 “母职” 到 “主权” 的身份翻转
- 如同男性对 “爸爸” 称谓的热衷,女性对 “妈妈” 的偏爱并非源于角色扮演,而是对 “掌控感” 的主动索取。在传统叙事中,“妈妈” 曾被绑定为 “无私奉献” 的符号,但现代语境下,它演变为 “全能支配者” 的象征 —— 从衣食住行的控制到精神思想的引导,恰似婴儿期母亲对生命的绝对掌控权。
- 案例:部分女性在童年母婴关系中曾处于 “失权” 地位,成年后通过成为 “妈妈”,完成对原生家庭权力结构的反向对抗,将 “被支配者” 身份转化为 “游戏规则制定者”。
- 女性主义视角:对父权秩序的隐秘颠覆
当女性要求伴侣呼唤 “妈妈”,本质是对 “父权主导” 的传统亲密关系模式的挑战。黑格尔 “主奴辩证法” 在此显现:男性心理退行至 “婴儿态”,依赖女性的情感供给;而女性以 “全能母亲” 形象,既提供滋养又掌握 “给予或剥夺快感” 的权威,在传统性别框架外建立了新的权力逻辑。
二、精神分析:欲望投射下的角色悖论
“妈妈” 称谓的双面性,藏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心理共生。
- 被支配欲的伪装:当 “主权者” 成为 “工具人”
- 拉康指出,“妈妈” 是婴儿欲望投射的 “象征性空位”,是满足自恋需求的 “全能供给者”。在亲密关系中,男性呼唤 “妈妈”,实则将伴侣拉入童年欲望框架,使其成为满足自身恋母情结的工具;而女性接受这一称谓,潜意识中是对 “被需要” 价值的确认 —— 即便扮演被动角色,也能通过 “被欲望” 反向掌控关系主导权。
- 阿康理论(欲望的他者性):女性的快感源于 “让对方因自己而快感”,如同通过 “学习技巧、购买战袍” 取悦伴侣,“被叫妈妈” 本质是通过成为对方欲望的核心,确认自身存在的主体性。
- “达咩学弟” 现象:以 “猎物” 姿态狩猎的权力玩家
- 网络热梗 “达咩学弟” 指称喜欢呼唤伴侣 “妈妈” 的男性,其心理机制可追溯至卢梭与华伦夫人的关系:幼年丧母的卢梭通过呼唤年长女性 “妈妈”,在 “臣服 - 支配” 的矛盾中获取情感满足。这类男性多存在原生家庭创伤 —— 母亲的严厉控制或情感忽视,导致其成年后通过 “主动让渡控制权” 来抵御存在焦虑,以 “弱者撒娇” 的方式实施情感绑架。
- 俄狄浦斯情结投射:精神分析表明,男性对 “妈妈” 的呼唤,是童年期 “独占母亲、排斥父亲” 欲望的成年转化,通过将伴侣代入 “母亲” 角色,完成潜意识中未被满足的心理补偿。
三、存在主义视角:匮乏时代的情感代偿机制
拉康提出,人的成长是持续 “丧失” 的过程 —— 从婴儿期 “全能幻觉”(哭即得乳)到成年后对社会规则的臣服,每一次 “丧失” 都留下心理缺口。亲密关系中对 “妈妈” 称谓的追逐,本质是对 “圆满感” 的回溯:
- 女性通过 “被呼唤妈妈”,弥补童年期被母亲掌控的权力缺失;
- 男性通过 “呼唤妈妈”,缓解原生家庭中母爱错位的情感匮乏;
- 双方在 “支配 - 被支配” 的动态中,共同对抗现代社会的存在焦虑 —— 正如福柯所言,当规训成为枷锁,亲密关系的 “羞耻互动” 便成了短暂逃离现实的精神出口。
四、结语:称谓背后的本质,是 “被看见” 的永恒渴望
无论是 “被叫妈妈” 的女性,还是 “呼唤妈妈” 的男性,其核心诉求从未脱离 “被满足、被关注” 的心理基底。当肉体欢愉退居次席,精神层面的确认感才是亲密关系的终极麻药。这种看似 “越界” 的称谓游戏,实则是当代人在情感荒漠中,为自己搭建的一座临时避难所 —— 在这里,所有未被疗愈的童年创伤,所有未被正视的权力欲望,都得以在 “妈妈” 这个充满悖论的符号里,找到暂时的安放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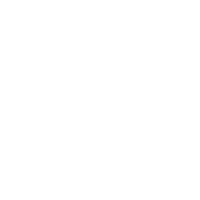

 180
180